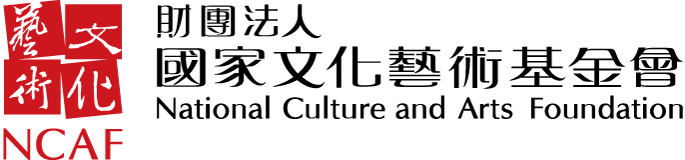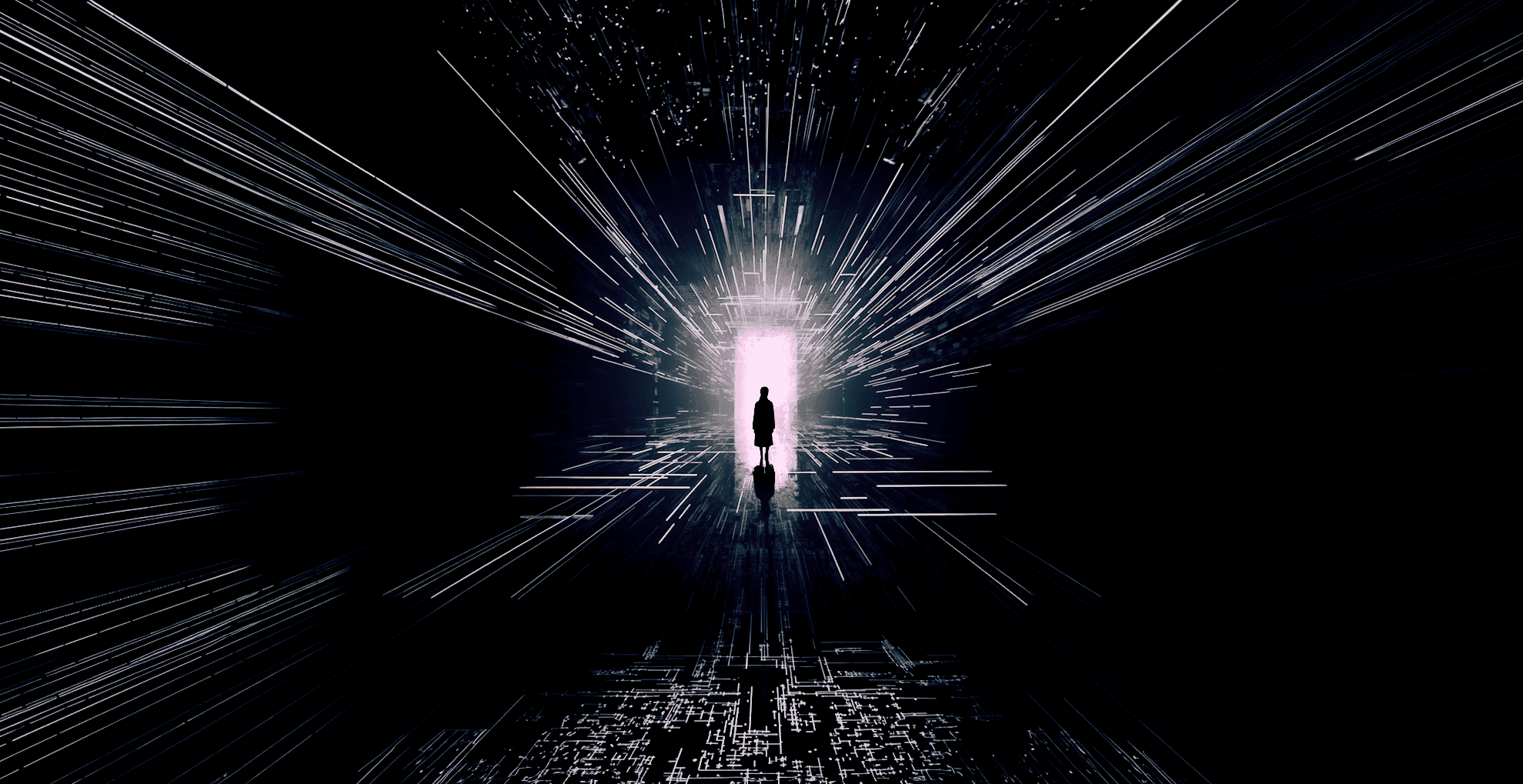
後VJ時代 Post VJ Era
VJ 已經不是過往 Video Jockey 的傳統指稱,相關從業人員或以此根植創作手法的藝術家們,也在尋求更新的自我定義與角色定位。VJ 一詞的多重性與多元價值,已經很難純粹用簡而言之的「地下文化」來概括其全貌。電腦技術和影像編輯軟件的發展,帶來更高質量且精細的視覺效果。在全球 Covid-19 疫情之後,結合演算藝術、3D 動畫、VR/AR、Web3、AI 創作……等,現已是百花齊放,創作者們擁有更多方式以表現創意和想法,從而影響電影、電腦遊戲與流行趨勢,為 VJ 創造更加多元的探索空間。我們難以忽視 VJ 文化在藝術性、技術性和創作性上產生的明顯變化,然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由此而生的宇宙大爆發時代?
編輯總監:張方禹 Aka Chang
主編輯:煙花宇宙 Endospace
企劃:KC Chen
序言
序言
儘管在編輯團隊的內部,「後 VJ 時代」也是個備受爭議的標題。
因為當我們談論「後VJ時代」時,意旨我們想拉出一道時間軸,指認其中一處轉折點,大膽定義:「從此以後,VJ/Audiovisual 和我們原先預想的不再相同」。
我們無法否認自 1980 年代以來發展的現場音像文化,如今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社群媒體的爆炸性成長,我們明確感受到它從充滿實驗性的初步概念,不僅走進文化工業中奠定自身位於產業鏈的角色,甚至逐步轉變為一種更為開闊的藝術型態。但我們想與創作者、場域、組織、行動者對談,談談從前、如今與或近或遠的未來。

燧人氏 Zuirens 由 2006 年開始以中文書寫關於 VJ(Visual Jockey)文化與 Audiovisual 音像藝術領域,不自覺將屆 20 個年頭,2023 年我們要推出以訪談為主的系列特輯。命題是「後 VJ 時代」。關於時代。先假定曾經有一個屬於 VJ 的時間線。燧人氏 Zuirens 或可大致描述某個段落的場景。就不從 VJ 開始發展的上世紀 70 年代說起了,我所經歷的背景大概是從 2000 年代中期開始,我看到的也是 VJ 從稀有到普遍再到標準化流程。當時電腦的效能逐漸發展到能夠負擔即時混合數位影像的工作,雖然一開始只有 320*240 和很高壓縮比的影像編碼,但隨著投影機的流明度一年一年提升,LED 屏幕的點距一年一年縮小,即時影像的處理也從 VCD 提升到 DVD 畫質並停留了一段蠻長時間。那段時間 Live 的實驗影像或許是門顯學,據說某藝大那段時期的畢業製作大部分都是選擇動態影像。到了 2000 年後期 VJ 的動態視覺幾乎已經是上到大型演唱會、商業活動,下至 Underground 地下音樂派對活動的標準配備, 同個時期全球興起了 3D Mapping Projection 的風潮,10 年間全世界對於 VJ Live 視覺需求更推升到一個高點,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記得有一些遺留在那段時間線的眼淚。曾經有一個滿載酷炫又免費日系素材的VJ軟體叫作 Motion Dive Tokyo,謎之版本很容易取得,那軟體就像是入門 VJ 的 Eye Candy,加料版的!硬體大廠 Pioneer 曾經出過一台可以用 DVD 來 Scratch 的 Player 叫做 DVJ-X1,但超貴,大家都是用自己的麥金塔 Power Book 來放素材。那時候最主流的影像混合機(Video Mixer)叫做 V4(Edirol/Roland),標準的四軌 Input 可能是兩軌電腦素材加一軌 DV 錄的現場畫面,再加一軌 DVD Player 的素材,帥一點的會用 VHS 錄放影機或幻燈片機,最後再過一軌給影像的效果器輸出!(RCA 的時代啊……)講到素材,那時候的 VJ 取樣(Sampling)範圍從 80 年代香港邵氏的武俠片到李小龍都有。最經典的 VJ 特效是萬花筒效果(Kaliedoscope),幾乎什麼畫面套上那上下左右鏡射對稱的特效瞬間都變得有了什麼。在當時有些 VJ 團隊會藉著釋出原創的 VJ 素材讓人免費下載使用來打知名度,但從來沒有人的免費素材像 Beeple 大大佛心供應的那樣質和量兼具,令人無比讚嘆!2022 年他把自己持續了十多年的創作集結成加密藝術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並在佳士得拍出近 7000 萬鎂的價格也一點不令人意外。那個時期的 VJ 看起來就像現場 Live 版本的 MTV 頻道,在各種音樂場景的現場即時剪接畫面,大量不設限地 Mash-Up 拼貼各種影像元素,節奏快速跳躍難以預測,風格更是難以定義。然而二十年一晃而過,2023 年燧人氏 Zuirens 在這條時間線的前面綴了個「後」字,成了後 VJ 時代。根據 ChatGPT 的提示,「後」的意思有「接替、繼承、下一個」,想要和前者作出區別的;又或是想要突破既有的框架,對抗它、超越它;但換個角度看後,也可能更具有包容性與可能性;一個相對較新的事物,想像它具有的動態性,擾動、變動、轉化著,打散固化的事物而非沿襲傳統。後 VJ 可能的關鍵字包括了 AI、遊戲引擎、大規模沉浸體驗、無人機展演、AR/VR/MR、機器人手臂等等,但或許不包括 5G 假議題~🤣我們想開啟一段對話的旅程,藉著和職人、創作者促膝聊天,拼貼這條屬於動態視覺、即時影音、音像藝術領域的時間軸線,持續紀錄此時間線上、線下的場景與姿態。VJ、Audiovisual、乃至 Mapping Projection 隨著時間移動或許不再是新鮮事,但職人曾經走過的道路就是生長而出的脈絡給予新晉創作者借鑑,人們也許不再稱呼自己是的身分是一名 VJ,但 Live Visual 即時操控影音的能力則是門基本功課,並且早已深植在各種創造領域中遍地開花。

儘管在編輯團隊的內部,這也是個備受爭議的標題。因為當我們談論「後 VJ 時代」時,意旨我們想拉出一道時間軸,指認其中一處轉折點,大膽定義:「從此以後,VJ/Audiovisual 和我們原先預想的不再相同」。我們無法否認自 1980 年代以來發展的現場音像文化,如今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社群媒體的爆炸性成長,我們明確感受到它從充滿實驗性的初步概念,不僅走進文化工業中奠定自身位於產業鏈的角色,甚至逐步轉變為一種更為開闊的藝術型態。 VJ,意旨從事現場視覺影像的相關專業人員,或以此根植創作手法的藝術家們,也有人稱其為音像藝術,或是各種仍在變動中的詞彙。唯獨不變的,是以科技工具來開展的創作多元性,以及影像必定與音樂有高度緊密結合的獨特藝術呈現,其所應用範圍,已廣泛到很難純粹用簡而言之的「地下文化」來概括其全貌:地下音樂場景的起落與演唱會的崛起,材料工程、硬體技術和影像軟體的高速發展,社群媒體的無遠弗屆。甚至在全球 Covid-19 疫情之後,掀起對於演算藝術、加密藝術、3D 動畫、VR/AR、AI 創作……等等,不得不「去現場化」的創作或維生型態,現場音像無疑歷經最為動盪的時代背景,創作者們被迫在最短時間內,尋求更新的自我定義與角色定位,雖然因此為其奠定更加寬廣的應用基礎,卻也使得自身發展已複雜到難以辨認其脈絡。 如今,會單純定義「自己是位 VJ」的人已越來越少,許多創作者早已走過這個階段,紛紛走向下一個身份認同,也有人開始將其轉為純粹風格美學的展現,就連維基百科上關於「VJing」的條目,也停在 2000 年後不再前進。 假使我們難以忽視現場音像在藝術性、技術性和創作性上所遺留的種種足跡,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在走過混沌的宇宙大爆發後的此時此刻?歷經多次的身份轉換與快速淘汰,我們又希望別人如何看待仍在其位的創作者?或更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自己?而不僅僅是盲目地前進。編輯團隊多次為上述議題進行討論,直至深夜,即便各有各的信念,但絕不否認現場音像所帶來的啟發性。這個計畫標題,便是在一次次的辯證之後,所定下的最終共識。在此次計畫中,我們會試圖將「後」和「VJ」拆開討論:「後」意味著我們不著重於過去的發展,而是透過焦點訪談,去描繪開始劇烈轉變的時間邊界,這也象徵著我們將盡可能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去看待,而是用多元的角度去吸收資訊。而當創作者們從地下走向地上,皆被賦予不同的任務與角色,於各個生態圈遍地開花,使用工具也大不相同,那麼「VJ」技術的應用範圍、風格美學上的發展、對產業的影響,與藝術呈現的新想像,便是我們去重新打開定義的重點項目。 因此,我們精選十多位,曾經體驗過、仍在從事中,或已轉型為不同型態的資深創作者們,我們藉由訪談,去拼湊隨著科技發展所產生的不同路徑,比如:「光」的藝術,動畫、程式、視覺、聲響、Projection Mapping、建築..…等,透過文字再現這些走進不同領域的創作者,其轉換的心路歷程與此刻的創作概念,可能都有屬於自己的「後 VJ 時代」,而我們的任務,便是以逐字稿的形式,忠實地呈現他們此刻的現況。 在編輯團隊的訪談過程中,我們察覺創作者因時常介於藝術、設計、商業應用和創新科技之間,往往易於遭受質疑:「文化科技在使用工具或選擇表現手法時,到底是不是有意識的、有靈魂的?還是只為了科技而科技、為了新鮮而新鮮?」卻同時又因為是新科技,便輕易被應用端視作時代新寵兒,被賦予必須緊緊追逐科技浪潮的任務,或是需要為展現新科技而刻意創作。 這樣進退兩難的處境,我們深有同感。然而,隨著訪談漸增,慢慢理解創作者的角色,已更加深入為產業鏈的關鍵環節,轉換為呈現型態更加完整的藝術家,或是朝著具有時代開創性的驅動者前進……在混亂之後,都漸漸有了各自的理解與答案。因此,這些資料註定沒有標準答案。我們更願意將文字視為擾動,促使自身去重新看待原本被固化的疆域,不用急於走進先入為主的固有標籤中,而能試圖以一個未定義的角色再度混合出全新的樣態。本期刊懷抱著這樣的初衷,期盼每一位讀者,都能在這個跨領域的時代裡,找到自己最舒適的棲身之所。
EP. 1
VJ 音像藝術創作者
#VJ
#Audiovisual
有別於一般訪談紀錄,此次燧人氏的探問更貼近於創作者對創作者的提問與紀錄。2023 年,世界甫走出 Covid-19 衝擊,是創作者可以回首過往的創作路徑,檢視當下自身狀態的極佳時機點,以對未來方向提出下一步的指引。我們期待著這些問答歷程會像是時間印記般被留存著,為若干年後其他研究者或採訪者記事、結繩,透過這些文字紀錄,梳理當代藝術家的創作脈絡與思考模式,及對時代的回應。

認識王新仁多年,看你的作品充滿著條理的數學邏輯,一直好奇為什麼大家叫你阿亂 (Aluan)?是哪裡亂了?我唸書時,有次做作業,連續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評圖當天,外系老師來找我聊天和討論作品,他就問「這個東西是誰做的?」,我當時意識沒有很清楚,沒搞清楚老師意思。我就回說「阿……亂做的」;意思指這東西「是我亂做的」。結果因為外系老師很好奇,跑來問我們老師「你們學校那個阿亂是誰啊?他東西很有意思耶!」,但老師也找不到班上有人叫阿亂,後來一直問,才問到是我,所以我後來就因為這好笑的誤會,而得到這個大家第一印象有趣的外號。阿亂今年發行了 Web3 系列「Automatic Messages」,關於這個作品,想請阿亂跟我們分享一下它的內容,以及請告訴我們你在這個作品裡置入存在或不存在的訊息。 《Automatic Messages #21》Aluan Wang (2023) 《Automatic Messages》除了是自動訊息/對話,也是自動性繪畫的意思;指以無意識的方式驅動身體作畫,但畫什麼不是自己的主觀意識在控制,而是在那邊被靈感或某一件事情觸發。我現在的身分是 Full Time Artist,每天都必須要做創作,大多數時知道要做什麼,但也有很多時候是不知道要做什麼,卻非得做些什麼的 Moment,那個狀態就很像 Automatic Messages。所以我就思考「我被什麼制約?為什麼我會無意識地寫一些東西?」,例如現在很流行的 AI、機器人議題,機器人的所有表述、行為就是有機器人三定律設定,它的人格特質或表述才會發生。那人類又是憑藉著收到什麼訊號,才做出自動書寫這件事情?扣回我過往在 fx(hash) 發表 Chaos Series(混沌/混亂系列)時的作品核心,有點像是雖然我在寫演算法去控制電腦程式碼,然而我在寫的時候是取決於那個太始之初,一切什麼都有可能的 Chaos。而這次作品看似抽象,但在這些幾何線條、繪畫筆觸,帶有點東方色彩的 Wabi-Sabi(侘寂)當中,它們的組成、布局其實是基於一個看不見的路徑才有辦法長出來;我用一個模仿植物生長系統的 L-system 演算法,作為每個物件之間距離、位置的概念,寫了一個路徑 Path,然後把那個路徑抹掉,不讓它被畫出來。這個不存在的東西滿重要的,就像東方所謂的留白,是由有畫東西跟沒有畫東西之間的強弱對比構成,在傳統繪畫裡面,留白是沒有辦法被言語形容的,藝術家可能知道怎麼做,可是很難跟人解釋;所以在我這個抽象繪畫裡面,它就是在背後隱藏著一個演算法,在說什麼地方該畫、不該畫。我們知道 Audiovisual(數位音像)是阿亂其中一項持續多年的創作脈絡,能否和我們聊一下自己是怎麼接觸 Audiovisual?第一個對外的公開演出是什麼樣的場景?當時的演出的情況大概又是如何呢?我最早是在 2002、2003 年讀大學時,那時我在看燧人氏的文章分享 VJing 一套軟體系統,好像是用 Flash 影片驅動的。當時還沒有 Motion Graphics 這個詞,也不理解什麼是 Audiovisual,但就很喜歡那個溝通方式,覺得一堆會動的平面視覺超酷。好不容易開始玩以後才發現對不到拍子,對不上就跑去玩塗鴉,沒繼續把更多心放在這上面。後來是 2008、2009 年念科技藝術研究所時,我從平面設計轉做動畫,然後再跑去寫程式;當時其他同學都是做一些很酷炫的燈光、硬體裝置,所以我就想到過去生活背景有接觸的 Audiovisual、VJing。開始做功課後,發現幾個國外藝術家非常有意思,田所淳、Zach Lieberman、Golan Levin、John Maeda,還有當時協助創辦 Processing 的 Casey Reas。最有意思的是日本藝術家田所淳,他當時來臺北藝術大學表演的內容,我覺得震撼了我們現場所有師生,包含王福瑞老師。田所淳當時表演的聲音、視覺是基於某種共構原理,像是在畫面上畫出一群蜜蜂,而蜜蜂移動時就是聲音;但並不是聲音、影像互相搭配,是由演算法驅動整個事情。尤其當時藝術大學的老師對於東西是誰做的標準很高,學生其實也沒有那種拿別人的音樂來放的事情,我們就是必須要整個東西都是自己的,所以我就覺得田所淳的策略很適合我;當時也很多日本人在做,包含岩井俊雄、坂本龍一從 1995 年開始,到後來池田亮司、黑川良一。而我第一件比較正規的音像作品,就是研究所 2009 年左右;花半年寫完程式碼後,又花一年半的時間去反覆調整,叫作「移動中的共鳴」。這件作品在 2011 年有去德國威瑪表演,總長度 30 分鐘,分成三個段落,全部都是用 Pure Data 所寫,所以也去了 Pure Data 的研討會;當時創作很 Hardcore,裡面所有的聲音都是 Sin 波、Cos 波等數學函式所生成出來的,超純,甚至比我後來很多音像作品都更純。過去在 Audiovisual 的藝術實踐,對現階段在 Web 3 領域的創作是否有影響? 現階段專注於生成藝術的你,如要再進行現場演出,是否會加入你在 Web 3 的創作經驗在演出中?比如:你在 Art Blocks 發行的系列「Good Vibrations」,是帶有聲音的生成音像作品,未來有可能發展成 Audiovisual Live 表演嗎?我早期的確是用 A/V 讓國際認識我。雖然我現在視覺型的 Gen Art 做得很好,可是很多現在臺灣年輕的朋友,或者是新的藏家,完全不知道我以前在做什麼樣的東西。所以我時常私底下都還是會提醒大家和我自己,不忘初心很重要;像我 Google 的頭像,就是之前在燧人氏辦的活動現場演出的照片。我第一個被國際所重視的東西《Good Vibrations》其實本來就是音像作品;它的機制早在 2012、2013 年我就已完成互動原理,當時我有30個實驗演算法的系列叫 A/V Lab,《Good Vibrations》就是其中一個;它當時叫《練習曲 étude》,有參與廣達基金會的「QA Ring:國際數位藝術展演跨域合創計畫」,也作為音像表演參加林茲電子藝術節。當時 Art Blocks 很多人都討厭東西會動,到現在整個生成式市場也還是很討厭東西會動,但我就很大膽地把它變成一件 Web3 作品。從我發完 Art Blocks 之後,可能會覺得我跑去做生成式藝術,但 Audiovisual 是不是生成式藝術的一支?也是!生成式藝術從 1960 年代發展到現在,其中就有分支在做 Audiovisual;可能是當時 Golan Levin 在 1998 年到 2000 年左右做的東西,再往前推,則是岩井俊雄跟坂本龍一合作的《Piano — As Image Media》;還有 Fujihata(藤幡正樹)也是影響深遠。而且它滿有挑戰性的。我們以前在理解生成式藝術的時候,我們追求的是 Frame Rate,追求的是每一個 Punchline,每一個音樂、畫面的點都對到拍,所以視覺畫面一定不可能太好,沒有那麼高 Quality 的「算圖」;追求的是很幾何、即時感強烈,互動感高。後來我發現從 2010 年左右開始,就有一套生成式藝術是長時間的,它的長時間並不是說在這一秒就是六十格,或要花一分鐘才算一張圖。它講究讓電腦像一個畫家,程序性地去繪圖,跟我過往在做的 Audiovisual 是完全不同的創作概念,所以我現在花了很多時間在做這個。但的確很多外國人常在問《Good Vibrations》有沒有系列作品,我後來有做一個 B-side,可他們想要問的是「有沒有更音像相關的作品」;只是這種東西在市場上面不賣,不管誰做都不賣。Audiovisual 就是沒有辦法像 William Mapan 一樣能夠獲得市場認可。 《Good Vibrations》#100 王新仁 Alung Wang 而 Max Cooper 又是另外一個狀態;但 fx(hash) 上面的 Agoston Nagy 跟 Shaderism,我就很佩服他們,他們超能寫,但他們就還是繼續做市場上不賣的音像;例如 Shaderism的《Sound Therapy》這個作品,我超級喜歡,聲音超好聽。不過我未來應該還是會繼續做音像相關的,因為音像反正做再好都很難賣,那 Audiovisual 這種比較有趣的就是實驗性質,反而可以市場上面試水; 例如我之前有一個本來要送《Turner Light》藏家的作品《AVLab 23》, 它也是 A/V Lab 其中一個音像實驗;所以我是有點想要把這 30 個初衷,至少做 10 個出來,或許之後我就會發行相關的音像作品。但我現在不太會想要做大型的演出;坦白說我現在身上背負著各式各樣奇怪的使命,所以我可能會把僅存的時間拿去做更有效應,更能幫助到所有創作者的事情,不太可能再花做兩、三年才能做出一個三十分鐘的表演,所以我應該不會專注在即時演出,可是實驗性質的音像作品,我還是很有意願繼續做。能否請阿亂稍微預測你自己的近未來?因為我們相信阿亂未來的動向或多或少都影響著這個領域的樣貌。近期的你還有些什麼計畫?我覺得 Web3 是具有革命性的,它是年輕人翻轉社會階級的一個方法,因為固有的階級已經沒辦法流動;但後來被搞爛而令人厭惡的 Metaverse、元宇宙,我認為它其實有階級流動的可能,至少很多人講那是夢想,我自己真的也曾一度打破這個階級。所以首先必須讓 Web3 它的基礎建設以及相關創作者,越來越多人能夠從這個新的生態裡面自食其力、謀生,我滿在意、希望推動這塊的。如果我們相信新世界充滿更多可能,那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讓人能夠做喜歡的事情活著,讓努力的人能夠有人支持他們,這是我現在正在努力的事情、目標。儘管這極度困難,可能比我自己的成功還困難百萬倍。雖然現在 Web3 市場真的超級糟,但我會想到過往做音像的時候,現在再怎麼慘,也沒有當時慘吧?前陣子有位加拿大藝術家 Matt DesLauriers 來臺灣,他在 Art Blocks 的《Meridian》和《Subscapes》賣出 3 萬枚 ETH,他也說過如果因為現在熊市而跑掉,假設下一波牛市回來,市場只會支持那些之前活在痛苦深淵裡面打轉的藝術家;就像當時 Art Blocks 第一波藝術家,Dmitri Cherniak 的《Ringers》,或 Art Blocks 創辦人 Snowfro 的《Chromie Squiggle》。我雖然沒有很早加入區塊鏈,但我做過很多 Open Source 的專案;台灣第二位在 Art Blocks 發行的藝術家吳哲宇,也是從 2016 年念大學到後來去美國念碩士,市場上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在 Open Processing 上面寫一大堆的教學。另一位 Open Processing 的日本藝術家大神 Takawo;2021 年發行《Generative Masks》當時大爆賣;他在 Open Processing 上面完成了連續 2000 天,每天寫一隻小程式碼的動作,堪比 Beeble 的 5000 天。另外一位 Art Blocks 的藝術家 Piter Pasma 也是雖然後來去做其他事情,但還是有在持續推動 Gen Art 的發展;這是很重要的堅持,因此我認為市場一定會回來。請問音樂對於阿亂來說是什麼,或說聲音對你是否存在著特別的意義?我寫程式時很難不聽音樂,我到現在都還是聽固定幾種曲風,第一個聽後搖;第二個聽噪音,但不是 Merzbow 那種噪音;比較像坂本龍一那種比較冷的電子。我只有聽這些才能夠冷靜下來專心寫程式,所以我認為音樂是構成我作品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我做完這次新作《Automatic Messages》的時候,我的好朋友還說「你要不要稍微換一下曲風?不然你那個東西看起來很壓抑」,所以我認為音樂百分之一百,一直都是我在創作中很隱性,沒辦法被彰顯出來的一部分。對於阿亂來說,甚麼是真正的即時(Real "Real-Time")?如果要達到很恐怖的 Hardcore,那就是 Live Coding,以前臺灣有一個創作者叫李駿,他從頭到尾在臺上同時表演寫聲音、影像,甚至三不五時還寫註解 Comment 告訴你「他在幹什麼」。這種 Hardcore 的方式是我以前追求的,但我現在比較不這麼做。(微笑)我現在變得超寬鬆,如果一個很厲害的 DJ 在舞台上根本沒打盤,就只是用 Slider 推一推、按 Play 鍵;可是他讓觀眾覺得「他在做真的」,他的動作跟音樂、Timing、Tempo 都對得起來,觀眾在台下同步感受到心臟爆擊的愉悅、快感,覺得很爽,那也是真的 Real-time 。數學在你的創作裡佔據著什麼特殊的位置嗎?我創作的原理始終都是數學,因為我是從寫函式、Function、演算法起家的。舉例來說,如果要表述從 A 到 B 之間是距離時,那個距離的結構有最佳、最短、最遠的路徑,有偶數、奇數拍的路徑;把它切成四等份,就是音樂的 4/4 拍;所以無論是距離、音樂,都是數學上的間隔、間距。這跟極限主義、數學搖滾很像,所以本質上我的創作就是基於數學,基於演算法的名詞「Interpolation(插值)」,在 0 到 1 兩個值之間,透過插值,不停補區間。對於阿亂來說藝術是什麼?如果回推到一切的起源,你為什麼選擇藝術創作?我認為是藝術選擇我,我之所以選擇藝術是因為沒有退路,唯一的退路就是掉下懸崖;基本上我的才華有限,當我做所有事情都比不過別人,都做不好時,選擇藝術就是我唯一覺得做得比別人好,自己也很喜歡做的事情 —— 我只要想辦法把它做好。當然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可以把喜歡做的事情做好,我還記得我剛學程式碼 5、6 年時,能寫出來的東西很有限,就是一堆很像 Illustrator 疊出來的幾何造型方塊;當時我不太能夠表達出我內心所想的,要等到學將近 6~9 年後,我才真的有辦法可以去做、去想一個看起來很好、複雜的視覺。 <EBB 2015> 王新仁 Aluan Wang 現場演出如果用簡單的話來總結,你認為屬於王新仁的藝術是什麼?這很複雜。比較快速的回應是,我的作品就是跟人們、跟時代對話的一種表現法;我覺得我的作品在當時的時空,很可能是滿適合跟當時人們對話的工具,所以我可能是在用說故事的方式,在跟我所有的受眾對話。我現在創作時會想很多事情,除了想自己的事情之外,也會想別人的事情;我認為創作者、藝術家是兩種不同的態度。如果是做 Time-based 時基藝術,或表演性質的內容,本質上就是說故事者;我沒有聽過任何一個說故事者,是不需要照顧、注重群眾的心情、心理。我可以負責任嚴肅地說,如果你開心做忠於自己的創作,然後專注在自己的創作領域底下,那你就是一個創作者。可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家,那肩負的社會責任包含作品有沒有跟社會溝通,創造的價值能不能幫助自己謀生。你必須要讓自己先抬頭挺胸的活著,如果你沒有達到這件事情。那麼我坦白、以及嚴格地說,你就是個創作者。 (微笑)

請和我們談談最近的狀態。在講最近的狀況前,稍微自我介紹一下,我本來是做 VJ、視覺統籌,2014 年後開始轉職導演、演唱會製作人角色。目前在必應創造擔任創意長,負責管理一個展演事業群,群裏面有各種與展演相關的工種與團隊,包含導演組、視覺設計、舞臺設計、燈光設計、音響設計、技術總監……等等,所以除了專案的創作之外,有一部分的時間在做團隊組織的規劃與管理。回到最近的狀態,因為疫情期間而取消或延期的演出,在同一個時間點冒出來,導致每個原本一年只服務兩、三個專案的團隊,都得在更短的幾個月內完成兩、三個專案;如果之前已經完成設計的內容,在當下顯得不合時宜,那就會變成需要重新製作 —— 所以覺得自己現在能抽出時間接受訪談真的很幸運(笑)認識春哥多年,早在你進入相信音樂體系之前,當時你的角色還是VJ,想請你和我們聊一下第一個對外的公開演出是甚麼樣的場景?當時的演出的情況大概如何呢?透過朋友介紹,我在 2007、2008 年以自由接案者的角色,接觸到演唱會的影像設計,當時發案的老闆,也是我入行的師父「龐奇視覺」的 Jeff 哥(傅強)。我最初只負責做影像內容,師父會讓我到現場看自己設計的內容所呈現出的演出效果。一段時間後,偶然有了參與到現場執行的機會;那是我第一次在控台作為 VJ,參與了五月天在小巨蛋的「離開地球表面」演唱會,播放〈最重要的小事〉這首歌的視覺;因為這首歌的影像是我設計的,視覺的進歌點我最清楚,再加上當時使用的軟體系統是 Resolume 2.41,我們還沒有所謂同步技術的概念(由 Program 送出 Time Code 碼,將視覺與燈光聯動播放的技術) 所以現場必須得同時有兩、三個人一起操作系統,人工同步;記得當時我緊張到手是發抖地在按鍵盤控制畫面。每個演唱會導演都來自不同的背景領域,現在還有和你經歷相似的新進導演嗎?春哥是從實際製作演唱會影像和執行現場 Live 視覺的 VJ 團隊開啟你的專業領域,這段過往是否影響你之後的工作模式?我在「相信音樂」製作部任職視覺總監時,還是一種導演、視覺兩組人會共同討論創作、創意的狀態,沒有非得是導演組先起架構,視覺組才能跟進的狀況;這可能是時代背景的關係,十年前的團隊編制不像現在那麼龐大完整,分工也沒有這麼明確細緻,每個人什麼事情都得學習,試著讓自己有解決事情的能力。我記得洋公(現必應創造執行長)說過:「製作組就是解決問題的人,大到演出內容,小到馬桶不通,都要能解決」;但現在的分工比較成熟與細微,習慣是讓導演組先去確定需求,把架構、論述、大綱這些資料整理回來後,再去找負責不同工種的視覺團隊來討論、分配該怎麼處理專案。雖然分工更明確,但我覺得「解決問題的能力」本質還是一樣的。所以現在分工明確的結構下,視覺創作者有沒有機會跨領域到導演組?機會還是有的, 只是需要被給予信任的空間,因為面對商務責任時,如果客戶明確想要某些效果,導演組不能用毫無規劃的「試試看」的方式去運作,必須先規劃好方向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去嘗試其他可能性。但我還是一直很期待能有更多類似我經歷的人出現,只要有合適的機會,就會嘗試讓一些適合的視覺統籌去轉換觀點做演出。我們知道隨著時間推進,每個時期你製作的 Show 都會有不同的製作概念並加入新技術。譬如多年前你曾和我分享過整個演唱會在流程上分成多個大段落的編排邏輯。能和我們分享你目前做演出、創作的流程與配置嗎?技術面的或是概念發想上。我認為演唱會現場最重要的三個元素是「傳達者(表演者)」、「接收者(觀眾)」、「被傳達跟接受的訊息(音樂)」;一個歌手就算只是拿著吉他坐在我們對面 50 公分唱歌,也可以算是最低限度的演唱會。但如果把歌手跟我們之間的距離拉開到 50 公尺外,就會需要演唱會產業的硬體工程來輔助,基礎任務是以音響、燈光、視覺等設備,確保表演者跟接收者之間距離可以被拉近、接收跟傳達是順暢的;再來才是傳達者怎麼利用技術去傳達觀點。過往我們嘗試把主題延展成有起承轉合的故事架構,讓現場觀眾像是在聽故事的人,藉由轉場接收觀點。但做久了人都會反骨(笑)所以後來我漸漸不在意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間必須要有銜接性,而是會去想傳達者跟接收者之間的關係,思考要如何讓接收者在每一段的感受、體感上是有層次的。如今遇到更多不同表演者、創作者後,我的思維也已經變得更沒有固定的建構流程,而且隨著時代推進,網路串流讓資訊內容更易於取得,觀眾感受演出、或各種創作的頻寬也在產生變化,例如參考韓國的流行音樂會發現,超過三分鐘的歌曲變得開始越來越少。甚至我現在也不太會和歌手一見面就說可以用分成幾個段落的方式來討論;會想先聽表演者本身對演出的期望,想要傳達給觀眾的資料、訊息有哪些,包含精神層面想傳遞的內容是什麼,再依照這些去思考如何建構有趣、有效的傳輸流程;做到目前,我覺得製作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幫客戶和團隊之間做集體創作的引導跟溝通。三年的疫情期間對於演唱會產業是巨大的低潮,當時有不少的節目製作轉往虛擬線上演出發展,甚而是所謂的 Metaverse 元宇宙虛擬空間演出。走過疫情之後,看似整個產業又動了起來朝疫情之前的狀態復甦,走過疫情前後,想必春哥是點滴在心頭,能請你和我們分享這段時間你的心路歷程嗎?前幾年疫情期間,整個業界都在不可控中,除了需要去海外國際市場跑動,維持資源運轉外,就是試圖去抓住一些自己可以運作的技術和創作;將來線上體驗勢必會是另外一種創作思維和產品線選項的媒介。但其實我更有興趣合作、討論的是遊戲產業,會希望大家的思維和格局都可以更開闊地去思考體驗經濟的其他可能性,去瞭解遊戲產業的創作人,例如小島秀夫、宮崎英高這些身為「傳達者」的知名遊戲設計師,是怎麼思考、建構作品企劃,安排玩家作為「接收者」、「反饋者」投入個人體驗的故事。這延伸到我們未來該怎麼思考演唱會在不同媒介上的創作。可惜現實很多具實驗性質的專案,如果沒有機會、資源落實運作,或是缺乏適合的 Artist 合作對象,就只能止於閒聊、想法。但只要業界不斷發生一些有趣、可以嘗試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仍能觀察到事情跟原本自己初步的想像有什麼落差;畢竟只要是有規模的商務專案,它預設的狀態和資源規劃,還是會希望技術表現的安排和結果可以被掌握、控制。這段回答感覺說了什麼,可是又好像什麼都沒說。哈~但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態,真實反映出疫情期間我們的感受吧!必應創造在華語演唱會文化裡佔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身為共同創始人以及現任的創意長,你對於團隊未來的視野在哪裡? 如果不考量太多成本技術等方面的問題,你想像過未來的演唱會是什麼模樣嗎?我想像不到,也不敢想像,因為一旦想像,就會給自己一個範圍;所以我覺得未來應該是有眾多可能性的平行時空,如果只選定一個方向,就會損失其他可能性;但在身為團隊主管的角度上,還是會試著提供一些方法、制度,讓大家可以思考這個題目。或許會產生各種天馬行空的答案,但其中有一定的機率會具有啟發性與開創性。因此比起個人去想像未來演唱會是什麼模樣,在我的職能、角色上,我更會傾向思考要怎麼讓團隊去想像這件事情,並且可以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出來。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你最近在看的創作推薦片單 (教學影片? 紀錄片? 或是劇 XD)以前我會看一些教學來提升技術能力,或透過動漫看一些新的影像創作獲得養分,例如我覺得《奧術》在技術、風格、講故事的能力、人物刻劃,各方面都頂天,這種就是休閒生活喜歡看動漫的同時,也刺激、衝擊創作想法的敏銳度,是可以一物多得的好項目。但最近這半年事情變多後,我喜歡看的都是一些比較療癒性的影片,像是韓國、日本那種去露營不講話的,也會看一些騎腳踏車、開車到西藏去旅遊的。有點像是在彌補自己沒辦法去,但也不會花時間去的心靈救贖,用《白日夢冒險王》來形容就是會想像,但我不會真的踏出那一步。所以比起過去覺得看紀錄片可能會得到什麼養分,我現在更想透過看療癒性的影片來得到更寬廣的心靈空間(笑)。音樂對你來說是什麼,或說聲音對你是否存在什麼意義?音樂大概就是我職業傷害的來源(大笑)因為我的工作屬性讓我必須什麼音樂都聽,自己也會盡量避免只聽一種音樂類型;但我當然有個人喜好,所以扣除掉工作需要聽的音樂後,回到我自己一個人對音樂的需求是我很喜歡聽舒緩療癒的北歐民謠,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可以更新我靈魂的更新程式,是可以重新修復我身為人的急救包。因為我是以「軟體」、「硬體」、「韌體」來看待人的結構;硬體是人的軀殼,而韌體有點像靈魂,它是和硬體綁定的一個內嵌架構;軟體則是外來的資訊、工具,包括增加人的硬體技能,或者是硬體運算的可能性;而韌體的擴充、更新,會讓人有更多運算效能去消化軟體需求的事情,也讓我身體的接收能力,可以重新被修復後,去處理複雜的軟體運作。我們在很多創作領域都會討論到即時性,尤其是與表演相關的領域。但在不同領域的創作者角度所詮釋的即時性彼此有所不同。想請小春哥談談看,關於你曾經製作執行經驗當中(也可以是曾經接觸過的作品),有沒有一種表現或演出,是心目中最理想的即時性(Real real-time)?也可以談談這個即時性的關鍵是什麼?雖然我們在一個線下即時發生的產業工作,可是演唱會產業最常被說的就是充滿遺憾,因為它只發生一次,時間點一過,所有人事物的狀態都會一起被確定,它沒有機會像拍片一樣可以重來,去找到想像中的最佳狀態。所以我們在現場,有時候快感都是來自於先預設好一些可能性,在掌握整體架構的可控運作外,保有一些不會偏離軌道的偶發性變化,讓現場其他參數、變數進來空間碰撞出活發性,產生一些有趣、稍微失控的化學反應,那狀態有點像是一個詞「精準的失控」。技術上最常做的就是 Live 畫面和 VJ 效果結合、現場觀眾的聲音參數、螢光棒亮度,這些雖然是我們可以決定的「項目」,但現場即時反饋的參數大小卻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覺得 Real real-time 應該是一種交給大家去自然形成的過程。只是在我們參與的專案裡面,沒有一個是可以百分之百交給大家自己去感覺的;這在設計師思維裡面的議題是,我會去瞭解表演者想要跟觀眾傳遞的訊息內容是什麼,Real real-time 和表演者要傳遞的精神有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如果要把它放進來設計,它一定是跟源頭的概念有關係,而不是我只想要技術性地去炫技。我其實很在意現在許多提案有很大比例是技術上可以奪人眼球,但卻沒有很強烈地去論述它們要觀眾接收這個很炫的技巧背後原因或結合的概念是什麼。 (但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單純的圖一樂,概念什麼的不是太重要~哈)但在我自己還是 VJ 時,我覺得我有一次在控台上得到 Real real-time 的高潮,記得是宥嘉在香港演唱會上表演歌曲〈金粉世家〉,合唱嘉賓是我非常喜歡的黃耀明。我弄了一個略微迷幻的視覺,然後把他們的 Live 做不同的效果,放大、縮小、疊影,演出當下,我手上的十幾顆特效控制器旋鈕會隨著音樂與舞台上的演出變化而轉動去改變影像與表演者的關係,我非常享受整個演出過程,甚至覺得我跟臺上表演者是一體的,非常舒服;旁邊有人跟我講話時,我完全不理對方,因為我不想要那個感覺被打擾、中斷,那是我在 VJ 生涯中再也沒有過的感覺 —— 是很值得被記下來的一刻。前陣子和你的老同學方序中聊到,你是少見的擁有一件事的決定權的人,卻願意在事情的一開始選擇先傾聽合作夥伴的想法。這部分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聊一聊。 另外你們兩位在過往的合作中,你會找序中來聊天,講故事。這是很特別的工作方式,是否也能和我們分享故事對你的個人或作品的重要性。他太客氣了,我跟 Joe 是認識很久的老朋友。因為我們設計師的思維、特性就是會在一開始先傾聽,蒐集需求、Source、資料。而在團隊有上百人的專案運作中,其實每個人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決定自己怎麼跟其他人銜接,怎麼跟大家一起施力推動事情。只是我的角色比較靠近核心源頭,我需要先指引方向給大家;但給方向跟給一個明確的長相是不一樣的,給方向是可以讓大家在這過程中,有很多可能性去朝著方向靠近,甚至最後走到一個屬於這個方向,但沒人想過的秘境;但如果給長相,大家就只會完成那個被明確想像的樣子。所以我是一個喜歡引導大家丟些突發性、可能性,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創作碰撞的人。因此給空間也是我不想損失任何創作思考的可能性。但這也不是每個案子都可以成立,也是有些案子用這種方式,團隊覺得茫然與無所適從;當我觀察到給團隊方向後,卻還是沒有辦法前進的時候,就還是會給一個明確的長相,直接告訴團隊,請幫我完成這個想要的樣子;不過只要能有選擇,我都還是希望可以先給方向,讓大家給一些想法,把我推到沒想過的地方。投身演唱會產業20年,是否會希望金曲獎增設展演性質的獎項?在從業人員的角度上,當然會希望可以得到鼓勵和榮譽感。但是不是由金曲獎來頒?我不確定。但我會期待未來有屬於現場展演產業的盛會,可以鼓勵大家交流;我們有參加過國外一些類似的活動,整體更像是一種國際上的媒合交流,現場可以接觸各地的軟硬體廠商、產業人士,例如 Lady Gaga、Adele 的製作人、舞台設計團隊 Stufish。所以無論是不是獎項,只要是跟現場展演產業有關,它對產業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催化劑;例如台北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陸續開設影視專業技術課程、燈光培訓計畫的管道,使更多人才知道怎麼投入這個相對封閉的產業,我們整體產業規模才會因此而更完善。當然一個帶有評選機制與鼓勵性質的獎項,也是符合產業永續發展的,但如果需要號召整個業界,自然也需要業界的領導者們先在適當時機討論,才可以有更好的下一步去討論現實狀況,例如誰有資格評分?報名機制和授獎範圍的項目是什麼?這些可能都需要一個不偏頗的官方機構當基礎來主導,才可以讓大家可以跳脫單一系統,重新為產業的格局思考。例如金曲獎的地位就是它有一個很高的中立機構核心,才會是整個華人範圍都可以參與的國際項目;而文化部下面有流行音樂產業局在鼓勵流行音樂這個文化被推進。但在現場展演產業,目前其實不確定哪個單位可以作為是主要協助的基礎官方機構。如果金曲獎未來真的願意先釋放一點空間,有試水溫的項目可以讓大家先有一個認知,知道其實有一塊外圍環節是和流行音樂產業息息相關的現場展演產業,它們與裝幀、MV 導演一樣也是流行音樂產業核心所延展的產業架構之一,我覺得這就已經是先幫整個產業的未來跨出一大步了。請告訴我們,對於楊宗錞來說演唱會是什麼?屬於楊宗錞的演唱會是什麼?身為觀眾,每次 U2 的巡迴,我都會想盡辦法飛去現場看,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可以重新釋放我頻寬、更新我韌體,讓我增加生命體驗感知度的過程。2017 年 Coldplay 在桃園的亞洲巡迴演唱會,業界很多人都有去,當時大家聊天時都是同一句話開頭,「音樂對了,就什麼都對了」。這是很根本的事情,例如我最低的期望是 Coldplay 唱〈Fix You〉,當這個期望被滿足,我就覺得我滿足了,也不會在意雷射燈光效果看起來是精彩絕倫或是俗氣花俏。因此從最低的心靈滿足角度來看演唱會,是可以極其簡單的。這也意謂著如果音樂夠強悍,對設計者來說,可以有更多留白的可能性存在;這也是很重要的根本,現在整個產業有一大部分是為了讓音樂可以有其他更多層次的體驗,讓你看過各種絢麗的多層次設計演出後,可以重新去理解這個音樂。但如果那個多層次的體驗不是為了音樂,就只是「花招百出」而已;所以我現在的設計過程便是在不斷地減少東西、降低干擾,如果音樂、表演者本身已經有豐富的細節,那就該好好地感受這些細節;就好比是在品嘗生魚片豐厚油花的原始風味時,簡單而克制地沾一點醬油才能保有純粹,過多多餘的佐料,都有可能會掩蓋與破壞我們體驗那最根本的期待。

我們找了一些你們過往的訪談,這一題似乎還沒有人仔細問過。想知道「NAXS Corp. (涅所開發)」這個名字的由來?在團隊成立的早期階段,我們大部分的作品都以網路社會的視角探索來生、宗教與儀式、輪迴以及與數位意識相關的主題,例如《Render Ghost》、《XATA》和《Afterlife》等作品。為了強調科幻特質,我們還加入了「Corp.」這個後綴,使整體概念成為一家提供網路來世意識儲存和體驗服務的公司。而「涅所」指的是涅槃之所,也是一個類似 Afterlife 的概念。在早期的作品中,無論是沉浸式聲光裝置、沉浸式劇場、MV 創作還是 VR 作品,通常會在末段使用濃煙、強烈閃光,或者視覺上快速穿越一個巨大且抽象的門或廊道,作為尋找「涅所」的嘗試。《Render Ghost》,VR 沉浸式劇場,攝影師:劉君韻。我們知道 Audiovisual 數位音像是涅所開發其中一項持續多年的創作脈絡,能否和我們聊一下第一個對外的公開演出是什麼樣的場景?當時演出的情況大概如何呢?2012 年,我們在當屆台北數位藝術節的開幕演出《DIVE》或許可以視為團隊最早期的音像創作之一。當時的團隊是「涅所開發」的前身 —— CBMI。我們是一群來自各個學校科系的大學生,包含商業設計、產品設計、服裝設計、媒體傳達系、戲劇系、建築系。在那段時期,我們積極參與了公館一帶的電子音樂派對場景,如 Organic 有機派對、太初有舞等,並開始在派對和電子音樂節裡擔任 VJ 或設計數位藝術裝置。Organic 有機派對,裝置與影像設計,照片提供:NAXS Corp.(涅所開發)。《DIVE》這件作品則是在累積了派對創作經驗之後,我們進行屬於自己的原創創作的早期嘗試。我們構思了一個對於小毛孩來說野心很大並且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作品,提案參加數位表演藝術節的徵選,結果理所當然地落選。然而,當時的想法引起了當時台北數位藝術中心(DAC Taipei)執行長黃文浩的注意。他把我們找到 DAC 聊了一會,並邀請我們為台北數位藝術節設計開幕演出。《DIVE》對我們來說,除了是一場 Audiovisual 演出,同時也是一個無人劇場作品。雖然沒有演員或任何表演者,但我們將燈光、雷射、影像、煙霧都視為演員。此外,我們使用鷹架結構搭建了一個具儀式感的對稱空間,讓觀眾可以自由穿梭其中。在演出的最後階段,我們打開了所有的煙霧機,使整個空間籠罩在濃霧之中,同時搭配頂部強烈閃爍的光線,試圖呈現一個超越想像邊界的世界。雖然這件作品還顯得青澀,但對我們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在 NAXS 後續發展的作品脈絡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DIVE》,台北數位藝術節開幕演出,照片提供:NAXS Corp.(涅所開發)。想請你們聊聊在 Korner 和 FINAL 的演出經驗,這些經驗是否對你們的創作帶來任何影響?在 The Wall、Korner 和 PIPE 參與派對裝置設計的早期經驗確實為 NAXS 後來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從儀式性的概念、雷射、煙霧、燈光的形式,到觀眾導向的創作方法,這些都與這些經驗有著極大的關聯。在 FINAL 的演出經驗其實不算很多,除了少數幾次音像演出外,我們也很榮幸能以海報設計的形式參與到 FINAL 發跡初期的階段。我認為 FINAL 提供了一個充滿可能性、敢於挑戰主流品味的空間,對於次文化的發展來說是一劑強心針。FINAL 對這個世代的音樂、視覺藝術和美學產生的影響肯定是非常深遠的。很開心看到一些以前喜愛的、感覺離我們很遙遠的藝人,都因為 FINAL 的關係慢慢出現在台灣演出;在這些空間演出讓我們可以時常跳脫出學院框架,以不同思維來發展創作與實驗。請和我們大概分享你們目前做現場演出的流程與配置?技術面的或是概念的發想上。現場演出的影像大多以 Unity 遊戲引擎作為技術核心。音像作品通常使用 Unity 製作畫面,透過 Spout 將影像送到 Arena 中,方便進行疊加效果,以及與其他非 Unity 素材混合使用。對於表演藝術的演出,通常涉及更複雜的技術,以《Body Crysis/身體災變》這件與澳洲藝術家 Harrison Hall、Sam Mcgilp 合作共製的跨國演出作品為例。我們使用 Unity 打造的線上遊戲世界作為串連台北與澳洲現場的橋樑。《BodyCrysis/身體災變》,舞者演出暨遊戲畫面,攝影師:Jordan Munns。首先,透過導播系統,將位於台北的落差草原樂團演出音像即時串流至線上遊戲和澳洲現場。澳洲舞者以樂團的音樂作為背景音樂進行演出,舞蹈動作則透過動作捕捉設備即時串流至線上遊戲中。參與線上遊戲的觀眾可以操縱自己的虛擬角色,在虛擬場景中跟隨關卡的敘事自由探索,同時觀看/聆聽台灣澳洲兩地線下演出的內容。「遊戲」形式的體驗一直是我們長期關注的方向。另外我們喜歡以「虛構的文本敘事」和「章節/符號」作為發展作品概念與結構的方法。在涅所的作品中,一直有很強烈的「重視觀眾體驗」的意圖。是否能談談與觀眾的互動過程以及敘事體驗在你們作品中的重要性。我們強調觀眾體驗的脈絡,部分源自於先前深度參與電子音樂派對的切身經驗,另一方面除了自覺不擅長處理演員之外,我們對於鏡框式舞台、文本對白式的劇場形式時常感到疏離,因此一路朝向更具沉浸性、互動性的方向前進。不論是沉浸式劇場、VR 作品,甚至後期的線上遊戲式體驗,這些作品類型少了觀眾的參與便難以成立。我們嘗試在敘事大框架下,讓觀眾感受自己成為作品中的角色,融入所呈現的世界觀之中。這個虛構的世界因觀眾的參與而推動敘事的發展,多名觀眾也有可能在共同參與的過程中,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彼此的演員。涅所有相當多線上演唱會及派對的經驗,並且都讓人印象深刻!是否能分享你們在 VR/XR 虛擬演出領域預期的發展和視野。儘管疫情已經結束,我們對於虛擬演出的未來發展仍抱持高度的期望與興趣。我們認為線上虛擬演出本身是一種有待開發的新型態展演形式,它的存在並非僅僅是為了替代無法實體發生的展演,因此虛擬展演的設計不應該只是對實體展演的模仿,而應該著重思考自身無法取代的特色。至於 VR/XR,目前似乎離大眾普及還有一段路要走。因此,如果處理線上演唱會類型的專案,我們會優先聚焦在沉浸式網頁(Immersive Web)的體驗上。但同時,我們也認為 VR/XR 必定是虛擬展演未來最有潛力、最令人期待的領域之一。若線上演唱會能在沉浸式網頁中實現輕便、快速登入的特性,並同時能瞬間切換成 VR 模式立即體驗不需要額外下載程式的話,將會是一個極佳的體驗流程。我們猜想未來觀眾在虛擬演出中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不僅只是在台下觀看的被動狀態,另外遊戲、虛擬演出、線上社群的界線會愈來愈模糊。我們知道涅所開發近些時間延伸出了涅所未來。能否稍微預測你們自己的近未來? 因為我們相信涅所開發的未來動向或多或少都影響著這個領域的樣貌。你們近期還有些什麼計畫?涅所未來成立於 2021 年,其出發點在於以公司的型態發展,經營固定的工作團隊與空間,希望挑戰更複雜、需要深度整合能力的中大型製作,並向外展開,開始嘗試和各領域的國內、國際創作者合作。目前,涅所未來鎖定兩大發展方向:分別為「線上展演」以及「VR」。通過多年的線上展演策劃、製作、開發經驗,團隊近期推出了「AUTOMETA」—— 模組化線上展演框架,以模組化的形式協助各領域的創作者或品牌打造獨具特色的遊戲式線上體驗,持續挖掘線上虛擬展演領域的潛力。另外,我們將繼續探索 VR 領域,持續打造具國際水準的特殊 VR 作品。除此之外,我們也在梳理「涅所開發」的全新架構,預計將以涅所開發作為核心組織,統整旗下不同子品牌:Future/Art/Lab 的發展路徑,以更寬敞但又精準細分的方式耕耘不同領域的文化內容。其中,Future 即為剛才提到的公司 NAXS FUTURE(涅所未來);Art 為發表藝術創作的品牌;Lab 則會嘗試各種跳脫藝術框架的實驗性計畫或者產品研發,例如去年推出的「Protoworld」Web3 線上創作者社群平台就是我們的第一個線上產品試驗。未來還有更多計畫正在醞釀中,有興趣的話歡迎關注我們社群上的動向!請問音樂對於涅所開發來說是什麼,或說聲音對你們是否存在什麼意義?聲音在我們的每個作品中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過去處理「儀式性」狀態的作品中。聲音與音樂的呈現不僅是引導觀眾進入更深層意識和旅程感的關鍵手段,更是創造深厚情感和獨特氛圍的重要元素。 對於涅所開發來說,什麼是真正的即時(Real "real-time")? 我們並不特別追求「真正即時」的表現,我認為重點在於整體活動體驗的設計方式,以及內容是否能引起觀眾的共鳴。舉例來說,如果辦一場全息 Michael Jackson 回顧演唱會,虛擬的 Michael Jackson 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即使大家知道這不是真人演出,只要內容設計得當,仍然可以成為一場精彩的演出。以我們過去策劃的「夕陽小鎮虛擬音樂節」為例,舞台上的演出都是使用預錄的方式呈現。然而,我們將演出設計為依照時間表限時轉播的方式,配合虛擬Q版藝人角色、生動的 3D 特效、光線變化、藝人自行錄製的特色影片以及與現場其他觀眾的互動等元素相結合,來達到即時體驗演出的效果。雖然不是「真正即時」,觀眾仍然可以在小鎮中獲得沉浸的音樂節體驗;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真正的即時性可能對作品有所助益,但有時在考慮現實製作成本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出選擇。這種思考方式或許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夕陽小鎮虛擬音樂節》,照片提供:NAXS Corp.(涅所開發)。能不能跟我們分享最近在看的創作推薦片單,ex 紀錄片、教學 ……《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墜惡真相》 (Anatomy of a Fall)、《燈塔》 (The Lighthouse)、《英村腦殘故事》(This country)。 對於涅所開發來說藝術又是什麼?如果回推到一切的起源,你們為什麼選擇藝術創作?如果用簡單的話來說明,你們的藝術是什麼?平時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如果要說起源的話,主要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近來則將創作視為一種與他人連結的方式,如果能透過創作結交各領域有趣的人,或者透過創作到世界各地探索,似乎是一種不錯的生活樣貌。
EP. 2
音像場域文化
半世紀以來,音樂影像編織於派對場景中。各類型音像、裝置、數位、表演藝術在獨有的地下文化中照亮著跨世代觀者的舞動,流動的認同裡探索、推動了多元可能,獨特的脈絡成為當代藝術蓬勃發展的動能火苗。
疫情的爆發雖使得上世紀的美好進入了靜止,各種限制措施對音樂和影像的體驗帶來了巨大挑戰,為了深入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將進行一系列訪談,邀請從音像活動組織、場地業者,一同探討對他們而言『疫後音像文化場景』的變與不變,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並且展望未來的可能。
Coming Soon
EP. 3
國外音像藝術創作者
上世紀的派對文化高潮,在那疫情無差別地攻擊的警鈴敲擊下時軋然而止,暫停了眾多產業、暫停了擁抱與一起舞動的可能,娛樂體驗在此浪中成為了奢侈,全世界的藝術家們、藝術組織們失去了與觀眾接觸的機會。
或許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跨越世代的時代性中,看看那曾有的潮起潮落,並期待那曙光淺露、復甦的節奏鼓譟於音像派對場景。
是否有些事已然改變?藝術創作者們在創作、表演等方面是否因應疫情有所改變? 我們期望透過第三個專輯,邀請國外的音像藝術創作者、場域文化組織分享他們對於『後 VJ 時代』的想法。
Coming Soon
『從此以後,VJ / Audiovisual 或與我們預想不再相同』 -燧人氏編輯團隊